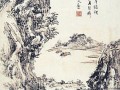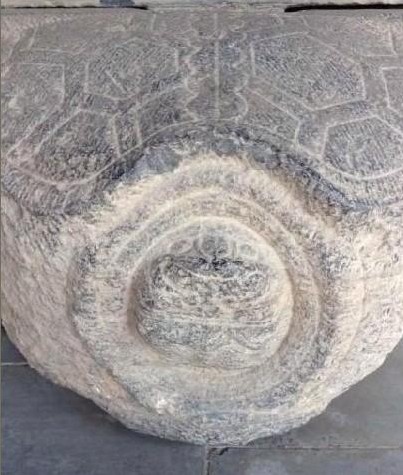《逃亡地主归来》

《减租会》
月黑风高的夜晚,逃亡许久的碾庄地主一家悄悄地溜回来,但不知道到了村里会有怎样的遭遇。
这幅画是古元用另一种手法表现国共合作时期的一个场景,那时候他的作品兼具叙事性、纪实性和艺术性。
21岁时,古元到延安碾庄做了乡文书,在艰苦的条件下创作版画。 《乡政府办公室》这幅画就体现了政府是怎样为人民服务的。画面中那个还没走进门的人是乡政府的通信员,政府的一级指令文件都是通信员跋山涉水一个村一个村送达的。那时延安很贫瘠,荒山野岭里有狼,所以通信员一定要带一条狗,否则会有危险。靠门边的那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不是坐而是“骑”在凳子上,姿势很随意,用腿卷着凳子腿扭着身子,地上放着行李卷,在那生活过的话就知道,这个形象真是很像陕北老乡。当时的背景是延安战区边区与敌占区边界呈拉锯状态,所以老乡在等着,估计要到国民党占领的地区做点小生意,干部模样的人披着棉袄,正在给他开过检查站的路条。桌子上的账本和记账的人要表现的是“账目清楚” ,那时候每一分钱都有记录。画面右下角,有个小脚妇女比划着在诉说,她来告状说自己受了家暴,认真倾听的干部就是我父亲古元。当时我父亲一听,这还了得,赶紧把妇女的丈夫找来。结果发现办的这第一个案子就是错案,他偏信了那妇女,来告状的妇女是个二流子,不仅家里活不干,生活作风还不好。从那之后,我父亲就知道一定要充分了解真实情况,再做出判断,人民才能信任你。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墙上的信插是个新现象,说明现在村之间有新信息需要流通了,桌上还放着延安当时的《解放日报》 。这幅画虽然简单,但是浓缩了当时政府的工作状态,表现了老百姓和政府人员的接触情况。
《逃亡地主归来》则是古元听来的一个故事。地主在土改时逃亡了,后来国共合作,民族矛盾放到第一位,有些地主可以回来,分了的东西可以还回来。月黑风高的夜晚,逃亡许久的碾庄地主一家悄悄地溜回来,但不知道到了村里会有怎样的遭遇。在五个人物之外,远景是碾庄的窑洞,静静地,表现的是他们晚上溜回来的情景。骑在第一匹毛驴上、走在前头的是一家之长的地主。很多人奇怪后面的地主婆胸前怎么挂着个十字架,那是因为在当时传教士已经进入到陕北传教。在神父传教过程中,做尽了坏事的地主婆希望获得心灵的解脱,皈依了天主教。跟着毛驴的一条小狗,不似陕北的土狗腿长、尾巴卷得特高、凶猛、擅跑,这是条宠物狗,是神父送给地主婆的,说明她的地位和经济实力很不一样。跟着地主婆的是大少爷,很多看版画的人不太明白大少爷两眉之间那道黑是不是刻的时候没刻干净,印脏了,其实大少爷养尊处优惯了,流亡奔波的生活让他受不了,那是拔火罐留下的一个印。一脸淡漠的抱着孩子的少奶奶,认为带孩子必须要坐着,所以想当然地坐在毛驴上,让大少爷走路给她牵着驴。最前面背已经弓得不行的人,是跟了地主几十年、已经麻木了的老长工,他不介意地主是流浪还是回来养尊处优,两耳不闻窗外事,也很忠心,这是很多最底层老百姓的精神状态。这幅画是古元用另一种手法表现国共合作时期的一个场景,那时候他的作品兼具叙事性、纪实性和艺术性。
知道了背后的故事,你会对那个时代更加了解。第三幅画《减租会》的环境是一个八仙桌,桌子底下有一个测量粮食的米斗,从画面上可以看出这时农民已经敢于一起进入地主家里。因为农民很穷,家里只有一张炕,有些缸、罐,所以这是地主的房间,有桌子、有画。从衣着上可以看出,地主与一般的村
民生活不一样,他穿卷羊皮袄子、云头的棉鞋,有胖胖的脸庞,一副吃饱穿暖的形象,也不是处理得面目狰狞妖魔化,而是看起来真实可信的形象。他用手指着天:“老天在上,第一,我儿子也参加八路军了。第二,我给你们地种你们才能活着,你们太没良心了。 ” ——我看过我父亲写的文章,这地主有名有姓,他身上发生的事情都有记录。在地主身后站着的这些人是中农,之所以在地主身后待着,是因为他们要看看风向,看减租会是地主占上风还是贫农占上风,他们好有退路。地主对面这几个贫农是搞土改的骨干力量,他们拿着账本,曾经被地主逼到无路可走没有饭吃的地步。最主要的是后面有个抱孩子的妇女,当时陕北有重男轻女的现象,通常这种场合妇女是不露面的,但是她抱着孩子站在后头,尽管没有说话的机会,却通过她的参与表达了对整个事情的态度。古元以“减租”为题材的作品当时有若干幅,这幅作品人物的布局、动态、表达的信息既是概括的又是生动的,木刻技法也是出色的,所以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本文系本报记者马李文博根据纪念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讲话70周年系列活动“父亲古元的延安木刻”讲座内容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